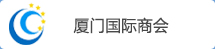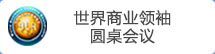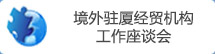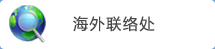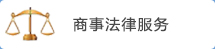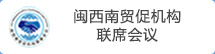[摘要] 财政政策要做的,不只是减税。一是供给侧的减税降成本要和需求侧的发债相配合,否则基层政府就运转不下去,养老金就不够。现在中国财政赤字水平只有百分之两点几,我认为需要上升到3%
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
从2015年年底开始,“供给侧”成为国家经济政策表述中的关键词。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开始供给侧改革,“释放新需求,创造新供给”;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”;2016年1月4日,《人民日报》刊登“权威人士”解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文章,引起社会的巨大关注。文章中,“权威人士”强调,中国经济转型的“窗口期”不是无休止的。
早在2011年,以西方经济学中的供应学派理论为基础,建议调控中国经济的声音已经出现。随后几年里,包括国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在内的一批学者,发起成立了“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”,提出了“新供给经济学”的理论框架。
顾名思义,西方的供应学派和国内的新供给经济学派,强调的都是经济中的“供给”一侧,认为此前长期用以指导宏观经济调控的凯恩斯主义,强调了需求、忽视了供给。
从凯恩斯到“供给侧”,变化是如何发生的?“供给侧管理”“供给侧改革”究竟意味着什么?时代周报日前专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。
强调供给侧,不忘需求侧
时代周报:2011年底,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就公开发表过一番“政府要用供应学派理论管理经济”的言论,后来一些学者也提出了“新供给经济学”。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?
周天勇:从2008年开始,中国经济开始下行。2009、2010年,在政策刺激下,又上去了一些,但政策刺激也带来了产能过剩、房地产库存增多、房价上涨、地价上涨等问题。
大概在2012年初,一些学者向中央提出,要消化2009年以来国家经济政策带来的后遗症,中国经济要进入“换挡期”;也有经济学者向中央提出,中国经济低增长将是一个常态,不要过于在意,要稳住阵脚,让市场调节。
从换挡期到新常态,我们采取了一些财政、货币政策,但经济增速依然往下跌。过去,凯恩斯主义里拉动经济发展的“三驾马车”(投资、消费、出口)着眼于短期需求侧的管理,经济过冷就多放货币、增加赤字、多上项目;经济过热就收缩信贷、减少赤字。
但2015年以来,经济调控遇到了难处。一方面,再来一轮刺激可能让过剩更加严重;另一方面,国家也担心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能让货币到达实体经济,而是流入股市或流到国外。需求侧的管理工具作用有限甚至不起作用了,这样就不得不转向供给侧的宏观经济管理。
时代周报:从需求侧管理到供给侧管理,这意味着政府的经济管理工作需要做哪些转变?
周天勇:一是供给侧的短期政策要和需求侧的短期政策配合进行;二是供给侧的宏观管理更着眼于中期的改革和中长期的技术创新、结构调整。理解供给侧宏观管理,我认为应该分三个层次:一是短期政策,二是中长期的改革,三是创新和结构调整。
短期政策的目的是给企业降成本,企业有了盈利空间后,可以多投资、多雇人甚至提高工资,这样一是增加消费,二是扩大生产—事实上,减下去的一定要转化为消费和投资的需求,这是企业减成本的政策要义。我们国家,非国有经济的比例在降低,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在降低,工资占GDP的比例在世界范围来看也比较低,金融部门和政府部门收入太高了,需求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,只有靠供给侧改革里的减成本才能解决。
具体到财政政策的改革,一是减税,比如增值税、所得税;二是提高小微企业的税收起征点,现在每月3万,能不能提高到8万?三是社保费率太高,占工资40%以上,可以降到30%。四是清理收费,从2014年的数据看,在土地出让金之外,政府的各种行政收费在32000亿元左右,企业负担沉重。
但财政政策需要做的,不只是减税。一是供给侧的减税降成本要和需求侧的发债相配合,否则基层政府就运转不下去了,养老金就不够了。现在中国财政赤字水平只有百分之两点几,我认为需要上升到3%。二是税收应该有增有减,比如财产性的税收应该要增,既可以缩小财富差距,也可以补充减税减掉的部分。三是需要变卖部分国有资产,补充养老金医疗金的缺口。
另外,企业成本压力还包括借贷成本过高,说是要发展直接融资,但看起来难度也挺大,从最近股市的表现来看更是如此。因此还是需要考虑一些短期措施。一个是降低基准利率;二是允许企业续贷,只要企业可以续贷,银行就不要抽资,否则企业的过桥贷成本会非常高,而且对一些企业来说,如果银行收回贷款后不贷了,就死定了;三是要认真考虑2008年大规模放贷时,地方政府协调的企业间联保问题,当时让好的企业替负债率高的、资产抵押掉的企业担保,现在可能有很多好企业面临银行的追缴,有可能发生系统性的破产、关闭停产;四是对那些负债率高、资不抵债、产能过剩的企业,要像上世纪90年代中期那样进行资产剥离和重组,对清算企业用破产重整的办法,把资产好的项目保留下来;五是需要修改最高法院对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解释,现在基准利率的4倍是合法的,但企业不可能长期承担4倍于基准利率水平(现在大概是24%)的利率,应该加上时间限制。我认为比如半个月、一年的贷款,24%的利率就是不合适的,也可以干脆一刀切,比如规定不能超过基准利率的两倍。
时代周报:你刚才说的供给侧改革的第三个层次,即创新和结构调整,该怎么理解?
周天勇:这些主要跟技术进步、产业升级、创业创新有关,比如中央提出的“互联网+”“中国制造2025”,也就是通过技术创新、新产业的扩张、新产品与新服务创造新的需求,来带动经济,起码说把流向国外的消费力收回来。
创新和结构调整是长期的事,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创新和结构调整一定要由市场来调节,政府少干预。比如说压产能,不是说政府去把产能关停压下去,而是需要考虑一些市场的手段,通过并购、重组、优化的方式。
当务之急是增加劳动人口
时代周报:当年英美靠实施供给侧政策扭转经济下滑,中国这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英美有无可比性?
周天勇:中央这次人口政策的变动,是最大的改革。这一轮经济下行,可能有60%的权重是由人口增速下降、老龄化、少子化带来的。
当时英美是滞胀,也就是经济下行、高失业率的同时伴有高通货膨胀率,但我们遇到的是“滞缩”,PPI已经连续45个月下跌。这是因为,当年美国人口变动是一个非常缓和的过程,而中国的生育政策导致人口下行非常快,经济上则体现在总需求减少导致物价下降、劳动力减少使得经济下行,阶段性失业却不严重。
所以首要的是尽快调整人口政策。估算下来,“十三五”期间,如果每年新增300万人口,就能新增1500万人口,增加的国民生产总值在6万亿-7万亿,到了“十四五”期间,这一数字可能翻倍,增加3000万人口。
然后是围绕人口流动的体制改革,包括土地流转以及和农民有关的教育、医疗、养老、户籍制度的改革。因为市民化的城市化,跟农民打工多年后告老还乡、或者在城市漂泊这种状态的城市化相比,产生的需求大得多,不会出现需求“塌陷”;土地制度不改革,不把房价降下来,农民买不起房子,居住方面的需求也上不来。事实上,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早提出过,人口流动带来经济增长提速,土地、房屋、人力资本通过流动重新配置,带来经济增长的新动力(310328,基金吧)。他提出,美国20世纪前二三十年的经济增长中,四分之一来自人口流动的贡献。
供给侧改革的第三个方面是金融改革。除了发展直接金融,重点是打破目前大中银行的垄断格局。现在,国民经济中的融资高利贷化之所以形成,最重要的一点原因是银行的高度垄断性。几千万买家对应为数不多的“中农建工交”银行,再通过各种服务理财信托等表内到表外的环节流动,垄断导致资金分布和最终的价格扭曲,所以中小企业贷到的总是高利贷资金。此外,大中银行为了规避风险,愿意把款先贷给信托、租赁、国有企业财务公司、村镇银行、典当行、小贷公司等,这些都成了从大中银行低进高出的非银行倒钱金融机构。其次,整个社会都有一种投资短期化、高利化、赌博化的心态,由此一些融资机构和单位允诺高利率、借新债还旧债的庞氏骗局式集资,开地下钱庄,也对利率的不合理上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消除国民经济高利贷化,根本上要放宽中小银行设立的数量限制。美国3亿人口,有各自独立的8000家银行,按照这个比例,中国应当有3.5万家各自独立的银行。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、地域辽阔、发展水平比美国低,未来也应发展到1万-2万家各自独立的银行。其中,特大和大银行包括中型银行的数量比例控制在1%-2%之间,绝大多数银行应当是社区为创业、小企业和居民服务的小型银行。为防止小银行再度集中化和仅为大企业服务,还应限制大银行和国有企业入股城市社区小银行。在金融体制改革的战略上,不能再采取变通和中间等有可能出现更恶劣后果的路线。
第四个方面是通过国有经济的改革,以及公私合作模式(PPP)等,盘活巨大的低效率的资产,吸引社会资金进入一些领域,使之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,包括一些价格改革,也是属于盘活经济。
- 市贸促会领导出席“2021年全国贸促...[2021-08-05]
- “弘扬传统文化,坚定文化自信”文...[2021-07-30]
- 厦门市贸促会领导带队走访企业[2021-07-27]